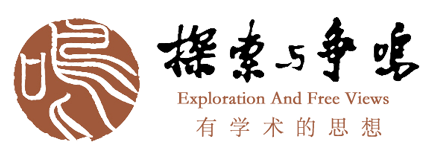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由于小说观念的阈限,我们常常忽略、淡化乃至曲解《狂人日记》在现代精神史、心灵史上的真实位置。《狂人日记》乃现代中国疯狂文学之开山、中国文学真实语言之诗性桂冠。它以小说名世,却终究要跨出艺术之塔,直抵人之存在真相,成为隐喻、抽象世界整体存在状态的“有意味的形式”。吃人游戏不终结,它就依然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目前具备文化人类学倾向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具备文化社会学倾向的“声音政治批评”处于张力与互补共存的对话关系之中。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张力和互补。第一个层面是在学理主张层面,即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动态关系。声音政治批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为文化政治从属于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则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于是形成了张力的关系。互补性则在于这两种学术思路的对话,在总体上深化了对上述三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思考,实则相辅相成。第二个层面在价值取向层面,听觉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听觉/声音的人文课题的复杂性的“求真”,声音政治批评的首要使命是“批判”,于是形成张力。互补则在于,两者都是从声音/听觉角度来考察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并探索改善之道,求真与批判是更高一层意义上“求真”的一体两面。
“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呈现出特殊的“隔绝”方式。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的对话,并非“补偿式”“交互式”或者“学科性”的联系,而是特定的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学术理念和方法视野之间的碰撞。没有“听觉文化研究”,还可以有“声音政治批评”;而没有了“声音政治批评”,“听觉文化研究”不仅会变成知识化的陈述,还可能落入英美文化研究预设的“快感陷阱”,沦为替声音的商品政治乃至文化政治的“听觉霸权”辩护的理论。王敦所倡导的“听觉文化研究”,表面上只是拒绝“声音文化研究”概念,实际上却在努力用“听觉现代性”这个话题,把“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考察声音变化和听觉经验重塑的自然史或考古史的故事,悄悄取代或不承认这个故事乃是且只能是由人在其社会政治语境中“创作”出来的意义丰富的版本。
区分“内核”与“辅件”,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内核”。体现和维护“内核”的外围“辅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则随时空场域的变化而改变“。辅件”的每一次调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出场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议程需要放宽外围、调整辅件。当代中国“解放议程”的设置,一方面在宏观上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内核”,另一方面必须依据时空场景转换,选择、调整和运用符合实际的“辅件”,既“不忘初心”,又“继续前行”。
大学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一种形态,其管理运行和治理同样离不开科层制。任 何制度都兼具两面性,科层制的弊端显而易见,人们往往指责、批评它,但还找不出合适的制度取 代它。科层制是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中的重要制度设计与管理运行规则,一方面促进了高等教 育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标准化;另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与高等教育组织本质属性相冲突的地 方,特别是科层化可能会导致官僚化与行政化。高等教育管理需要正确运用科层制度,提高高校 管理效率。
计算社会科学与大数据的结合,将扎根真相指导数据挖掘,一方面有助于修补资料挖掘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与理论指导算法。以如何在中国风险投资产业中找到产业领袖为例,建基于在复杂网中寻找最具有影响力结点的方法,首先,需要基于业内访谈和德菲尔法,得到关于“产业领袖”的定义和业内公认的名单,用以验证之后数据挖掘的模型结果是否有解释力。然后,用清科数据库的VC共同投资数据建立动态的产业结构网络,计算各项网络指标。最后,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找到由动态数据直接进行分组的合理方案,从而验证有现实意义的寻找“产业领袖”的指标。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定性以及定量资料收集,提供了大数据资料挖掘的扎根真相,这使得过去做声音、图像、地景之类的大数据研究有了更多议题、方法和理论上的发展空间。计算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正是不断地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算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上的扎根真相之间往往复复地对话,使得算法越来越接近扎根真相。
怎样对待领袖人物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近年来,如何对待列宁的政治遗产,在国内外颇有争议。我们既不能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不加辨析地神化列宁和列宁主义,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用它作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也不应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应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分析列宁的言和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留下的政治遗产,今人理应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
如果说《新青年》烹调了一道“民主”“科学”大餐,那么《学衡》奉献的则是一桌“示正道,明大伦”的人文盛宴。遵循自由和理性的旨归,并同样立足于关怀未来中国的现代性走向,两个文化群体着力于评文学、说文化、论学风、谈教育,以此为支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新青年”志士如同鲁迅笔下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猛士”“学衡”同仁犹如宗奉“儒行”之忍辱负重、外柔内刚的“绅士”。无论是“猛士”还是“绅士”,作为“不可以不弘毅”的“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任重而道远”的道义扛在了肩上。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化发展而言,他们的对话与争辩是异常可贵的,因为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进程中形成了难得的张力。恰恰是这种张力,为文化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了原初的动力。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既需要“猛士”,也需要“绅士”。
回顾十年来的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可以发现两大变化:一是在哲学研究/哲学史研究中以哲学创造为取向的哲学研究取得了突破,出现了不同进路与风格的典范性作品;二是经学研究的出现,改变了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版图。哲学创造面临着的哲学与哲学史、中国与世界的张力,反映在儒学研究中就形成了“儒学地说”与“说儒学”等不同言说方式。经学研究的出现可能造成政治与教化、思想与制度之间的连接,从而为文明论的儒学研究提供前提。文明论的儒学研究作为一种整合的视角,它可以超越儒学研究的分化与支离状况,从而构建一种具有文明论承担意识的哲学。
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是贾平凹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亦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为此,复旦大学中文系特邀请评论家在上海召开专题研讨会。《探索与争鸣》杂志拟于2018年第6、7期分上下两辑刊发相关评论,全面、深入呈现与会评论家的精彩观点。在下辑中,杨扬教授探讨了贾平凹小说的“以山为本”的晚期风格——历史感强化,叙事淡化,对人物进行非聚焦式的描写,同时强化对意蕴空间的开拓;宋炳辉教授从“世界文学”的视野里考察了《山本》,一方面认为贾平凹小说最具中国性,另一发面又提出了贾平凹式的创作该如何同时兼顾异文化的接受这个问题;刘艳博士梳理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文学“史”观的变化,并将《山本》置于这一脉络中探讨其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分析了这种文学“史”观对于小说叙事形式的影响。杨剑龙教授着眼于《山本》的人物形象,认为小说是要建构一部秦岭人物志。